写作 中外作家笔下的美食
本文转载自腾讯文化 编者按
“吃”虽是细枝末节,却也是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,反映在文学中,前有袁枚谈小吃,后有汪曾祺说五味,小葱拌豆腐的清雅,也值得一遍又一遍地细说。不独中国如此,外国名家在写作时,也会不惜笔墨地赞叹糕点的芬芳和果酱的甜美。但许是由于传承的差别,看外国作品中的食物描写,总觉得不够满足中国读者心中的味蕾…下面随文化君一起看看中外作家都是如何描写美食的吧!
中国作家写美食《汤包》,作者:梁实秋,中国著名散文家、学者、文学批评家、翻译家,国内早期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之一。
玉华台的汤包才是真正的含着一汪子汤。一笼屉里放七八个包子,连笼屉上桌,热气腾腾,包子底下垫着一块蒸笼布,包子扁扁的塌在蒸笼布上。取食的时候要眼明手快,抓住包子的皱榴处猛然提起,包子皮骤然下坠,像是被婴儿吮瘪了的乳房一样,趁包子没有破裂赶快放进自己的碟中,轻轻咬破包子皮,把其中的汤汁吸饮下肚,然后再吃包子的空皮。没有经验的人,看
着笼里的包子,又怕烫手,又怕弄破包子皮,犹犹豫豫,结果大概是皮破汤流,一塌糊涂。有时候堂棺代为抓取。其实吃这种包子,其乐趣一大部分就在那一抓一吸之间。包子皮是烫面的,比烫面饺的面还要稍硬一点,否则包不住汤。那汤原是肉汁冻子,打进肉皮一起煮成的,所以才能凝结成为包子馅。汤里面可以看得见一些碎肉渣子。这样的汤味道不会太好。我不大懂,要喝汤为什么一定要灌在包子里然后再喝。《豆腐》,作者:汪曾祺,中国当代作家、散文家、戏剧家,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。豆腐最简便的吃法是拌。买回来就能拌。或入开水锅略烫,去豆腥气。不可久烫,久烫则豆腐收缩发硬。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里的上上品。嫩香椿头,芽叶未舒,颜紫赤,嗅之香气扑鼻,入开水稍烫,梗叶转为碧绿,捞出,揉以细盐,候冷,切为碎末,与豆腐同拌(以南豆腐为佳),下香油数滴。一箸入口,三春不忘。香椿头只卖得数日,过此则叶绿梗硬,香气大减。
其次是小葱拌豆腐。北京有歇后语:“小葱拌豆腐——一青二白。”可见这是北京人家家都吃的小菜。拌豆腐特宜小葱,小葱嫩,香。葱粗如指,以拌豆腐,滋味即减。
北京人有用韭菜花、青椒糊拌豆腐的,这是侉吃法,南方人不敢领教。而南方人吃的松花蛋拌豆腐,北方人也觉得岂有此理。咸鸭蛋拌豆腐也是南方菜,但必须用敝乡所产“高邮咸蛋”。
高邮咸蛋蛋黄如朱砂,多油,和豆腐拌在一起,红白相间,只是颜即可使人胃口大开。别处的咸鸭蛋,尤其是北方的,蛋黄浅,又无油,却不中吃。《少小离家老大回:我的寻根记》,作者:白先勇,台湾当代著名作家,白崇禧之子。代表作《蓦然回首》等。
桂林米粉还真充满了无敌的诱惑。尤其是干捞粉,米粉圆而润滑,肥而油亮,口感鲜嫩而又韧性;那金灿灿的锅烧,入口又香又脆,加一些卤牛肉片,然后根据各自口味撒上葱、蒜米、香菜、酸菜(一般有豆角酸、竹笋酸和泡菜酸)和红辣椒—那种辣香味你在外地是绝对不到的。《饮食男女在福州》,作者:郁达夫,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、散文家、诗人。代表作《故都的秋》《春风沉醉的晚上》《迟桂花》等。
福州海味,在春三二月间,最流行而最肥美的,要算来自长乐的蚌肉,与海滨一带多有的蛎房。《闽小纪》里所说的西施舌,不知是否指蚌肉而言;白而腴,味脆且鲜,以鸡汤煮得适宜,长圆的蚌肉,实在是香味俱佳的神品。听说从前有一位海军当局者,老母病剧,颇思乡味;远在千里外,欲得一蚌肉,以解死前一刻的渴慕,部长纯孝,就以飞机运蚌肉至都。从这一件轶事看来,也可想见这蚌肉的风味了;我这一回上福州,正及蚌肉上市的时候,所以红烧白煮,吃尽了几百个蚌,总算也是此生的豪举,特笔记此,聊志口福。《谈宁中国美食作家推荐的食谱
波人的吃》,作者:苏青,与张爱玲齐名的海派女作家。著有长篇小说《结婚十年》,散文集《浣锦集》。
宁波的毛笋,大的如婴孩般大,烧起来一只笋便够一大锅。烧的方法,如油焖笋之类还是比较细气些人家煮的,普通家里常喜欢把笋切好,弃去老根头,然后烧起大铁镬来,先炒盐,盐炒焦了再把笋放下去,一面用镬铲搅,搅了些时锅中便有汤了(因为笋是新鲜的,含有水分多)。于是盖好锅盖,文火烧,直等到笋干缩了,水分将吸收尽,始行盛行,叫做“盐烤笋”,看起来上面有一层白盐花,但也决不太咸,吃时可以用上好麻油蘸着吃,真是怪可口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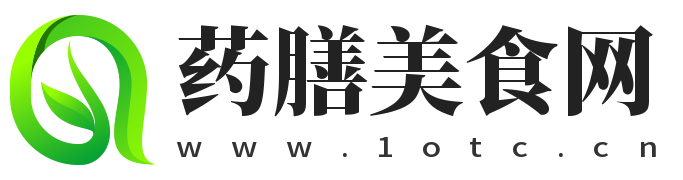

发布评论